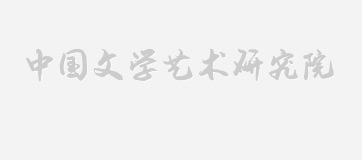文艺理论
美学研究
时间:2023-03-27 11:02:34 来源:原创 作者:曾克平 点击数:212548
赵八爷的四把剃头刀
文/曾克平
赵八爷名理,原属王姓。
母亲赵幺姑娘家无丁,弟媳付素珍生下七仙女,遭人白眼,村里上年纪的老人背后议论她是女人中的次品,生下来的都是赔钱货。
王氏家族人丁兴旺,赵幺儿与老公商议可否将幼子王理立嗣给娘家的弟弟赵乐于为子,丈夫仁义点头允喏。
村里有点老八股的赵太爷捋着胡子戳赵乐于的脊梁骨,骂他不懂“三纲五常”:“立嗣是立给辈分相当的侄子为嗣子,不得立异姓为子而乱族规。过继是可以的,把自己的儿子给没有儿子的人家或亲戚的儿子做自己的儿子,叫过继。”
多大一个事,换汤不换药,都是跟别人姓跟别人做儿子。农村人对立嗣和过继都不看好,要么家庭比较贫寒,要么过继人家无后。
好在王理是给滴滴亲舅舅做儿子,没人说三道四。
赵乐于请当地懂天文地理的读书人,查询老皇历选择适合‘添人口’的黄道吉日敬香磕头,向家中老人和神堂供奉的列祖列宗牌位一一跪拜,祷告庇佑平安吉祥,并对将来的老人赡养,家庭财产等问题立字为据。
王理开始一老鼻子不快,怄了一肚子气,凭什么要我改姓,大哥二哥未必比我金贵。这事由不得恁王理较劲,快过去了大半年,他才不情愿地改口喊舅舅赵乐于叫爸,喊舅妈付素珍叫妈。
时间长了赵理感受到了改姓的优越性,在本家虽然是老幺,有哥哥姐姐罩着看着,但丢人现眼的是长期穿破烂衣服,前面两个哥哥长高了他就捡旧的,光臀的裤没少穿,以前他最乐意去外婆家,现在是赵府名副其实的小祖宗,太上皇,他开始慢慢地产生获得感。
孩子是母亲身上掉下的一块肉,哪有不心疼的,平时很少回娘家的赵幺姑变得频繁了,有事没事去一趟。
赵乐于心里象明镜似的她姐姐怕付素珍虐待儿子,付素珍早就明白当姑姑的心思,生活中对赵理另眼相看,穿的吃的玩的赵理优先。物极必反,特殊的照顾引起了姐姐们的强烈不满,她们对付这个过继来弟弟的办法,孤立,包括在外受人欺服了,姐姐们也不闻不问。
被人孤立的日子不好受,赵理哭着要母亲一视同仁。
过分宠信一个人,会让这个人失去更多的爱。赵幺姑明白了这个道理,开始规劝付素珍不要对赵理无原则的迁就。她心里一块石头落下,儿子在赵家不会遭歧视。从此赵理与姐姐们和平相处,找到了家的感觉。
赵乐于对孩子的管教是放任自由,想干啥就干啥,老子天下第一。赵理逃学是常态,不仅自已逃学还带着村里的孩子称霸一方,打架撮祸,告状的人来了一批又一批。
六十年代,农村人认为读书无用,有点学问说是臭老九,知识越多越反动。学门手艺,跑到哪里都可混口饭吃。
赵乐于在这种思想支配下,带领儿子到邻村剃头匠学手艺。拜完师,师傅给赵理一把刀,一个葫芦,赵理除了帮师傅做家务看孩子,就是用剃头刀刮葫芦,葫芦皮刮深了刮浅了,就得挨罚挑五担水。
付素珍对儿子学剃头持有不同意见,俗话说“养儿不读书等于养头猪”,姑姑把儿子托付给我就得象亲生的一样待,应该读书,人从书里乖,剃头能剃出状元郎。她反对无效,暗地做过一件遭人唾弃的事,女人嘛头发长见识短,没人去认真计较。
徒弟徒弟三年奴隶。
三年后,赵理有了为顾客洗头,围围脖,剃头、刮脸,剪鼻毛、掏耳屎的资格。赵理手聪是个当剃头佬的料,村里人当面夸他的手艺比师傅强。
恭维话听多了,赵理自然很满足,决定另起炉灶搞单干。
赵家村有2000多人口,他家住村子正中央,是人员最集中的地方,便在家门口挂出“赵理理发店”牌子。
村里人需要赵理,离不开赵理,他的口碑不错,大人小孩见了都是赵师傅前赵师傅后。剃头是村里腾出来为大家服务的主要劳动力,所以剃头不用花钱,计上工分年底兑现。在不耽搁村里人正常理发的情况下,搞点外水没人说嫌话,比喻出行剃阴发,孝子给点利是。那时的利是没红包,给包香烟几个鸡蛋是对手艺人的尊重。赵理不隐瞒地说:“鸡蛋自给儿吃了,香烟大家伙儿抽了。”
烟民们出来做证:“是的,是的,烟酒不分家嘛。”
也许是农村文化贫乏的原因,不抽烟闲着没事干,所以抽烟的人多。抽的都是喇叭筒。随手撕张报纸,裁剪成长方形,从烟袋里捻出自家种的叶子烟丝,呈斜线一头粗一头细地匀在纸上包好,而后送上嘴角粘上口水,左手掌握烟体,右手把多余的纸捻成蒂轻轻一转,一支喇叭筒卷好,揪掉纸蒂擦燃火柴,吸口气叭叽、叭叽的样子很贪婪,瞬间缕缕烟雾漫溢整过屋子,散发的烟味很浓很呛人,呛得妇女眼泪直流。
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,剃头不算体力活,有小资产阶级享乐主义嫌疑,理所应当是专政对象,但赵理的理发店未受到冲击,照样挂牌营业。
隔壁李村的造反派不服气,找上门来闹革命:“我们李村的剃头佬都挂黑牌游行了,你们赵家村未必是攻不破的资产阶级司令部,不打倒赵理发,决不收兵。”
“人熟理不熟,你李村人凭什么跑到俺赵家村发号施令,要赵师傅下地劳动改造思想,不是你们说了算。”赵家村是大村,红卫兵战斗队有几十人,统一戴着袖章,穿着土裁缝做的黄军装,腰里扎的皮带五花八门,站在一起很整齐很威风,在气势上压倒了李村。
两支红卫兵小将站在村界之间,拔剑张弩,文攻武卫,形势十分严重。万一事情闹大,赵理脱不了干系,剃头佬见多识广,他对父母亲面授机宜:要他们赶快通知两村有亲戚关系和通婚家庭的人赶快救火。自己挑着剃头工具一闪一闪来到现场。
这剃头佬的担子一头是个长长的圆笼子,里面有一个小火炉,上面放个很大的黄铜脸盆,让水始终保持一定的热度,底部有三根支架,其中一根向上延伸顶部有根横杆,用于挂荡刀布和毛巾。另一头是红色油漆的长方形凳子,凳子腿之间有三个抽屉,一个抽屉放钱,第二个和第三个抽屉放围布、剪刀等工具。
赵师傅从容地把这剃头佬担子放在两队红卫兵小将中间,笑呵呵地拿出当时很时髦的“游泳”牌香烟,挨个儿边发边说:“这事因我而起,李村的红卫兵没错,该打倒的一定打倒,还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。从今天开始我把剃头佬担子放到田间地头,与贫下中农一道下地劳动,谁要剃头就喊一声,赵家村的老少爷们同不同意,再说我剃头也是听毛主席的话为人民服务,没有不劳而获呀!”
赵家村的红卫兵小将坚持赵师傅挂牌理发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,赵家村的事由赵姓自己管,不得由外村人干涉。这时两村沾亲带故的村民也来了,一个劲地拖着自己的子女回家,别在外惹是生非。
一场即将发生的武斗不欢而散。
李村的红卫兵回去后继续让村里的剃头佬下地劳动,接受改造,彻底肃清资产阶级的残余思想。村里男人的头发长了无人理,似乎恢复了大清政府的统一发型,蓄得可以梳长辫。
有人相亲或要外出,偷偷跑来求赵理剃头,赵理不推辞,村里红卫兵睁只眼闭只眼的视而不见。
赵师傅如此受人尊重的原因是他遵守职业道德,一生四把剃头刀不离左右,一路风雨陪他走来。
这四把刀明金金亮晃晃的剃头刀,分工明确,放置有序从不错位,刀刀锋利无比,风吹断发。
第一把刀。剃癞痢头的专用刀。什么是癞痢头,现在的伢子不懂,就是癞子,癞子也不懂,是过去一种常见的头癣,特别是头皮因剃头容易被感染。癞痢头是剃头传染的主要途径之一。由于成人对真菌抵抗力较强,而儿童较弱,所以头癣多见于儿童。唉,怪事!赵师傅发现自己的专用刀消毒后无缘无故地不见了,这种事发生过几次。一把剃头刀三角钱。以1962年为例:一角钱可买三个烧饼,三根油条,两只半冰棒;一元钱可以购买1斤7两猪肉,8斤大米,1斤7两鸡蛋,7尺平布或4尺斜纹布,50盒火柴,可以买十根蜡烛。
赵师傅除了心疼三角钱,关键是需要时掉链子,找不理癞痢头的专用刀。急得大汗淋头,只好用备用刀临时抱佛脚,剃癞痢头一刀下去血糊脓肿,不可来回反复进行,不然剃头的儿童害怕再剃头。赵师傅理头癣的刀特别快,也不嫌弃癞痢头脏,总是轻手轻脚,理完后还用杨树须烧成的灰加点薄荷与菜花油调匀,敷在头上止痒效果特好,剃完头对使用的工具进行消毒处理,晚上高温蒸煮,凉干分别放置,所以赵家村的小孩子得癞痢头的极少。但是赵师傅丢失癞痢头专业刀的谜一直没揭开,放在剃头箱里咋就不翼而飞了呢?
那天,付素珍要老公把米坛最后剩下的几斤米腾出来好清理坛底。米缸一般用的是四川榨莱坛子,防潮祛湿不生虫,一米多高的榨菜坛子可装百十斤大米,女人手臂短快见底的大米舀不出来。
赵乐应了声,就去弯腰侧身伸臂朝缸底舀米。奇怪!这坛子底部哪来的金属碰撞声,心里十分纳闷。这时舀米的赵乐于突然一声惊叫,只见他从米坛里拿出的右手指,鲜血喷射式的淌流,场面十分吓人。
付素珍哭喊着救人,还不停地用头撞击房间的木柱,非常懊悔地说:“都怪我,都怪我啊,赵理的剃头刀是我藏起来放进米坛了的,我压根忘记了藏剃头刀的事。藏刀是不想要儿子为长癞痢头的剃发。”
打断骨头连着筋,赵幺姑听说娘家弟弟手是被弟媳割的,抓了只母鸡与老公一道,准备兴师问罪地数落弟妹一顿:你这女人咋这么狠心。
心里有事步子快,三公里路程半个时辰就到了,刚踏进门坎赵幺姑就看见弟弟手缠着绷带还留有血迹,板着脸正准备发作。
赵乐于笑着把发生事情的前因后果说了一遍。听得赵幺姑怒气消融,绷紧的脸渐渐放松,
赵理得知母亲藏匿剃头刀的善意。
老公原谅老婆藏匿剃头刀是为儿子好。
流血事件反而融洽了特殊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。
第二把刀。故人剃头的阴刀。何为阴刀,就是为逝者理发。老人走了,子孙必请理发师为逝者理最后一次发。行话叫做剃阴头,人生苦短烦恼多,怎奈皈依自然何,化土随风凡世事,一刀了断阴阳歌。无论半夜三更,还是刮风下雨,孝子求你理阴头你去不去。遇上这事赵理二话不说背上木箱就岀门,理完阴发给逝者施点粉化谈妆,看上去脸带笑容,孝子贤孙高兴,偷偷塞上几包烟,赵理不客气,收下走人。
第三把刀。剃胎头的贴心刀。那可是个细活,细皮嫩肉的马虎不得。赵师傅喜欢闻小奶巴子的奶腥味,遇见漂亮的月母子,即兴调侃几句或讲段民俗故事,听得月母子害羞地笑。剃胎头不能一次性完成,中途小孩要吃奶,有时哭有时闹,赵师傅比月母子还有耐心,不骄不躁,打出各种手势或者用泼浪鼓逗弄月窝里的伢。
月窝里的伢一逗就笑,高兴时把衔在嘴里的奶头吐岀去又吮进来。赵师傅趁机说:“快吃,快吃,不吃我来吃。”也许是赵师傅无意,也许是有意,听得产妇红着脸,端上放了红糖的四个荷包蛋犒劳赵师傅。
这事被传了出去,越传越玄乎,传出好几个版本,外乎不了一个“情”字。
一传:赵师傅利用职业之便,勾引良家妇女,趁奶伢剃完胎头吃饱睡觉了,便与月母子腾云驾雾。是村里尖嘴婆亲眼所见。
又传:月母子见赵师傅眉清目秀,耐不住寂寞,顿时心生邪念,将一只奶头塞进奶伢嘴里,将另只多余乳汁的奶胞用力挤压,有意射向赵师傅的脸上和敏感部位。赵师傅醉了,猴急猴急地又被村里尖嘴婆看见了。
村里人不信尖嘴婆的话,久而久之调侃赵理的绯闻闲话也就越来越少。
第四把刀。给普通人和残疾人使用的爱心刀。对于腿脚不便或患有疾病的顾客,只要捎个信招之即去,有时把患者背到自家的转椅上,边讲故事边理发,剃头刮脸,掏耳剪鼻毛,接骨正位,捏、拿、捶、按,传统手法一样不落,这头剃得舒舒服服,舒服得在转椅上安然酣睡。
赵师傅荡刀与众不同,荡出的声音有节凑,啪啪啪地象唱儿歌,就这么荡几下,刀刃变得锋利多了。
荡刀与磨刀不是一回事。磨刀不误砍柴功,磨剃头刀最考验师傅的真功夫,正面磨几下,反面磨几下,用力均匀,来不得半点虚伪,想偷懒躲懒磨出的刀不好使,否则刀锋不利刃卷,现在的美发师谁还会磨剃头刀。
你说说,这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剃头佬,要打倒靠边站,劳动人民是不是一千个不答应,一万个不答应。这话是几十年前的事,李村人要赵理下田劳动,赵家村的红卫兵不服,差点和李村打起来。
岁月老人跟赵理开了个玩笑,当年的赵师傅变成了赵八爷,因为他上面有七个姐姐,故称八爷。
赵八爷68岁了闲不住,在背街的地方租间房,挂着十分陈旧脱了漆的“赵理理发店”牌子,从农村开到城市。八爷收费公道,无论什么发型一律十元,排队按先来后到的秩序。剃头的全是头发花白的老人,他们说不是图便宜,是找挖耳屎、剪鼻毛、刮脸、刀锋洗眼
的感觉,用热毛巾敷脸,软化毛囊,剃头刀吱吱吱的响声,就像一曲催眠曲,最不愿听见赵八爷围脖一抖说:“好了,下一位。”
到了这把年纪赵八爷心里急,想招个徒弟教他手艺,风放岀去好几年没人求学。
等候在一旁要剃头的田老头说:“八爷,你看正街上的理发店,一个个把头发染成红、黄、蓝、白、绿的,男女学徒不比顾客少,去那洗个头30,理个发50,女人染次发少说一百块,这是理发吗。”
你别看赵八爷整天乐呵呵的象个老顽童,也有发愁的时候,他跟田老头说:“年前我申请想把传统理发,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起来,不然再过几年就没人传承了,到时候你们这些老家伙谁跟你们刮脸,挖耳屎。报告上送了,批文下来未获准,理由是剃头的发展形势很好,要理发有美容美发店,要挖耳屎有专业的采耳中心,要刮脸去面膜,唉。”赵八爷叹了一口长气,埋头去理发。
起初赵八爷想把手艺传给儿子。
儿子不干,不肯学的理论一大堆:“谁还跟您削葫芦瓜,您的十多样传统手技都分叉了,分成若干个行业。挖耳屎,美称:采耳贴心屋,接骨正位,名曰:理疗中心,招聘的全是美媚按摩女,染发染鬓,雅号:美容美发厅。您看看隔三岔五的按摩院跟鸭棚(小餐馆)一样多,累死个人的传统理发谁干。还要我学快失传的什么刀锋洗眼,谁见过这门古老的技艺,是的,这么神奇的古老技艺,堪称刀尖上起舞,玩转刀锋,需要快、准、稳。说出来都吓人,刀锋洗眼之前,先固定上下眼皮,然后用锋利的刀片伸进眼里,贴着眼球轻轻划过,再用铁制的圆棒,轻柔的在眼里来回扫动,洗完了都说舒服,眼睛更明亮了。老爸能用刀锋洗眼确实值得敬佩,但一个如此危险的技艺,您敢教我不敢学。”
赵八爷想着儿子的一番话,心里在打鼓,找谁接班当传承人呢。
田老头见赵八爷不吭声,换种说法说:“八爷,你得好好地健康地的话着哦,不然,我去阴曹地府的那一天,谁跟我去剃阴发,你起码要活一千年。”
“我……我……我不成了祸害。”赵八爷瞪了田老头一眼。
“怎么是祸害呢我的八爷。”
赵八爷露岀一副苦笑,说:“你要我活一千年,不是祸害是什么,只有祸害才能活一千年。”
作者简介:
曾克平(笔名:湘客),湖南华容人,自幼随父迁徙湖北监利,现居石首。
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,中国散文学会会员,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,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闪小说专委会会员。2019年度中国闪小说十位新锐作家之一,湖北省“书香门第,耕读人家”获得者,湖北省“非遗”三国故事传说传人,出版散文、小说(长、中、闪等集)共15部。
地址:湖北省石首市文化和旅游局(笔架山路178号)
邮编:434400
电话:15927879745(含微信号)